
张修枫:张修枫,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TU Darmstadt)社会学博士,2001-2008年在上海大学社会学专业就读,完成本科硕士学习。现任中国民生投资集团中民嘉业战略投资部负责人,并出任亿达中国(HK.3639)、理工环科(SZ.2322)和FLI Global等多家境内外上市公司董事。同时,兼任德国绿色城市学会理事,并被聘为多家地产研究机构的专家和评论员。
本人是2001年进入上大社会学学习的。记得刚入学的时候,拿到的第一本书就是《春风桃李二十年》,读着一篇篇回忆系史的文字,对社会学系和社会学有了个懵懂的印象。师长们对本系的历史非常自豪,借着二十年的故事,给当时还是新生的我们许多嘱托,没想到那么快,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
我在上大社会学读了七年书,切身感受到了连绵吹拂的春风,见证了学科的发展壮大。个人也受益颇多,不单单是社会学课程的内容,教授们的为师为人也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借又一个二十年的契机,记叙一些跟师长们有关的个人回忆,希望能够为上大社会学的“集体记忆”增添些素材。
打开社会学的大门
考大学的时候,我原本的志愿是心理学,因为打小就对跟人有关的事情感兴趣。可惜,由于色弱的缘故,不具备报考的资格。倍感失望的我将大学专业指南翻来覆去地研究了很久,惊喜地发现了有一门叫作“社会学”的学科,尽管似懂非懂,但社会好像就是人群的集合,因此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当时最知名的社会学所在的上海大学文学院。但是,入学后发现,身边的同学大都是被调剂到文学院的,除了混日子谈恋爱的,很多同学都准备着转专业或考插班生,要不就是在积极考证的,似乎没什么人对专业感兴趣;同时,当时的文学院刚在低年级试点大学科教育不久,选修的课程有点杂,即便上过了《社会学概论》等基础课,还是对社会学一头雾水,我填志愿时的满腔热情受到了打击。
大一结束的那个暑期实践学期,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仇立平教授主持的一项社区调查,希望能够增加些对社会研究的直观感受。带我做调研的,是仇老师的研究生——当时刚读完研一的金桥学长。调研的具体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跟着学长一家一户地敲门,当时的学长特别腼腆,经常被拒绝,从早到晚跟着做访谈挺累的。调查过程中的所见所闻,跟我作为在上海长大的孩子所习以为常的社区环境差异很大,而问卷设计中的很多问题又看似很无聊,当时的我不理解其中的意义,各种迷茫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就冲动起来给仇老师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把专业的选择、学习的困惑和调研中的一些体会,一股脑儿地写了出来。
几天后,仇老师约我去办公室聊聊。当时的仇老师还没有白发,但平时严肃认真的模样早就有了“仇爷”的气场,“被约谈”的我特别忐忑,都有些后悔写那封又长又琐碎邮件。仇老师告诉我,非但他本人认真地读了我的邮件,还在系务会上以此为案例跟其他老师分享了学生的焦虑与困惑,非常欢迎这种师生沟通方式。他认为,我在社区调研中所产生的差异感就是一种“社会学问题意识”的起源,并由此鼓励我继续保持社会学兴趣,还给我讲解了社会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等等。现在想来,跟仇老师的这次聊天,仿佛是社会学对我打开了大门,体会到了从生活经验到抽象理论,再回到现实关怀中来的思考乐趣,坚定了我学习社会学的信念。
此后,仇老师一直持续关心着我的学业,有时课后会找我聊聊天,有时会发邮件给我分享一些文章。甚至于,在一次专业课考试的时候,身为监考官的仇老师特意走到我身边来看我答题的情况,而他越“慈祥”地看着我,我就越紧张,成了我考得最“大汗淋淋”的考试。后来,也是仇老师建议我,学习社会学要真正入门并进阶的话,还是要寻找一个让自己有“激情”的社会现象切入,带着问题去读书做研究,于是才有了我对于体育社会学的选择,并拜入了陆小聪教授的门下,开启了另一段深厚的师生情。
“新教师”vs.“老教师”
在千禧年初的时候,还有一批“老教师”是学科恢复建设后“半路出家”转到社会学来的,他们的学识功底和研究经验都非常丰富,但在今天看来,真正经过学科体系训练,即具有博士学位的老师并不多。
我们入校后的那几年,正好是系里面开始大力引进博士人才的时候,张佩国、刘玉照、董国礼、陆小聪、苏红、张文宏、刘春燕等一批具有名校和海归经历的博士教授们差不多都是那个时候先后加盟的。当时,学生们还开玩笑地说,这些老师的“校龄”比我们还短,是我们看着进校的。印象特别深的是张敦福老师,他的面试试讲就是在我们班级,全程用英语给我们讲“进化人类学”,好像是关于猩猩和灵长类动物的性行为与群体关系之类的内容,直接把我们都听傻了,但“不明觉厉”,对这些新来的老师都有莫名的崇拜感。
这批老师的到来,对于学生的影响其实挺大的。一方面,他们都很平易近人愿意花很多时间跟学生在一起交流,比如刚来时的刘玉照老师瘦瘦弱弱地背着双肩包,很容易被误认为是高年级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常常跟学生们一起在食堂吃饭聊天,大家就容易走得很近;另一方面,这些老师们带来了前沿的理论学说,比如张文宏老师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理论,都是当时教科书上没有的知识,对年轻学生充满了吸引力。当时,最热闹的就是大家积极地参加博士老师们组织的各种读书会,好像最初是刘玉照老师和董国礼老师各自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研究生本科生都混在一起,不仅仅在教室和会议室,还常常去草地上,甚至在屋顶上边喝酒边读书。后来组织读书会的老师越来越多,参加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氛围似乎就没有原来那么好了,但学生之间还是会相互交换书单,甚至打听各个老师的“奇谈异论”,真是怀念那段开心的读书时光。
随着“新教师”的到来,有一些“老教师”似乎是主动地让贤,将核心的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都让给新老师。在这个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跟胡申生教授的聊天。
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胡老师是上一代教师的缩影。在《春风桃李二十年》那本书中也记载了,他几乎参与并见证了上大社会学恢复建设前二十年的全部过程。事实上,熟悉胡老师的人都知道,他本人在文史思想方面的积累是很深厚的,文笔和口才都非常了得,而他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参与主持了很多社会调查,在家庭婚姻方面积累颇丰。我读本科生的时候,胡老师在系里的事务不多了,仅留下了一门《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主讲课程。而且,除了利用他在学校的行政职务给系里的项目提供支持之外,他几乎不主动参加学术研讨类的活动,也有意识地逐步减少带研究生的数量。
由于参加辩论协会的缘故,我跟当时还担任指导老师的胡老师有很多接触的机会。有一次聊天,谈到对于系里新来的这些老师们的看法,他说,“xxx等年轻老师跟老一批教授不一样,他们的观点很新潮,有些我也不认同,但你们学生要多跟他们学习,他们是受过系统训练的,熟悉西方的理论,代表了学科的方向,……,不管怎样,现在有那么多博士来了,对社会学(系)肯定是一件好事,要靠他们来推动学科的发展,我们老教师,肯定是跟不上他们的发展了……,但我对自己还是有要求,我也会主动看看最新的期刊杂志论文,我要能够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研究什么,就可以了”。
后来,我多次留意到,在社会学系内部不怎么发声的胡老师依然在很多对外的场合介绍并推广上大社会学,提到前沿学科领域的时候也是如数家珍。此外,还时常能在媒体杂志上看到他发表的评论或文章,依然是他擅长的谈古论今,但时不时地会引用一些新的社会学概念。我想,这也许就是新老教师的传承,也是上大社会学发展的脉络。
两种类型的社会学教授
也许是因为社会学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学科,社会学教授们个个都是个性鲜明的。毕业十周年的时候,组织同学们集体回过一次母校,才知道学弟学妹们已经公然地将各位老师的性格概括成“昵称”了。在此,我想特别描述一下沈关宝和顾骏两位老师,在我的心目中,分别代表着两类典型的社会学教授。
沈关宝教授是典型的学院派,他在社会学恢复建设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地位是学界共知的。可惜,我们上学的时候,为了鼓励年轻教师,他亲自参与的授课并不多,只保留了《社区分析》这门课程。沈老师上课,没有教材没有课件,往讲台上一站,笑嘻嘻地就讲开了,从社会热点到工业革命,从经济改革到现代性的变迁,从亲身社会调查的经验到方法论范式的辨析……沈老师讲课好似闲庭信步一般,深入浅出地把古典与现代、理论与现实都结合了起来,对于经典社理论学说和名家学者的学术故事信手拈来。听他讲课非但不觉得枯燥,课堂笔记记下来之后就发现逻辑是一层一层非常清晰的。这样授课的老师,是我在求学生涯中只遇到过的唯一一位。
我撰写这门课程的课程论文时,逐渐意识到,沈老师之所以保留亲自教授这门课,不单单是因为他作为费老大弟子所传承的社区研究传统,而是“社区研究”实则涵盖了“传统共同体vs.现代社会”这个社会学的经典主题/理论张力,作为一种研究路径或分析维度,也能够包容定量与定性的实证研究经验。多年来,沈老师始终坚持教授“社区研究”这门课,其实是他个人社会学视野的浓缩。也许,就是因为我在课程论中呈现了以上的逻辑,沈老师竟然给了满分的成绩,这大概是我初中毕业后直至念完博士,唯一获得过的满分吧,让我受宠若惊。
我印象中的沈老师是一个内敛含蓄的教授,他不太在学生面前表现出个人的喜好,但是修完这门课后,我能感受到沈老师对我的关心和肯定。每次见面都问我读了什么书,并主动提议推荐我去欧洲念书,说读社会学就应该在西方语境中学习。尽管,我最后去德国念书并不是沈老师直接推荐的,但他对我的鼓励一直给了我深造的动力。遗憾的是,听闻先生离世的时候太突然了,刚回国不久没来得及送别,也没有了给他汇报学习成果的机会了。
若要跟沈老师正统的学院风格比起来,顾骏教授可能就是“玩世不恭”的教授代表了,不仅在言论上常常语出惊人,而且他的研究对象也常常是“非社会学”的。其实,顾老师刚从华师大转入上大的时候,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老师了。学生们都喜欢听他讲课,因为他的讲课比他上电视的演讲更精彩,但是他给学生打分的时候严厉得不得了。论文答辩的时候,大家都躲着他,我曾亲眼见到有学生被他点评哭的。在读本科的时候,我也有点“怕”他,能不选他的课就不选他的课,但是喜欢去蹭课,去听他跟各种理论学说或专家观点的“抬杠”。
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无法躲顾老师的课了,因为“古典社会学理论”这门基础课是他主讲的。但是,跟其他教授不一样的是,顾老师让我们讨论古典理论,不允许我们评论前人评论过的内容,必须用自己的观点,甚至还要求我们的课程论文里面不允许出现参考文献。由于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做讨论,顾老师要求当时从本系保研的学生(即他的学生沈启容和我两个人)带头,分配给我们俩讨论的还是孔德——古典社会学家中相对最陌生的那一个。在一周的时间内,我们俩几乎读遍了能读到的所有文献,最后绞尽脑汁地从孔德的人道教为切入点,“自说自话”地讨论了一番实证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庆幸的是,这番“自说自话”竟然通过了顾老师的考验。若干年后,读到过一篇理论社会学论文探析的就是类似的话题,才发现顾老师的良苦用心,是在逼学生做原创的理论思考,可惜那篇课程论文没有深化成一个完整的成果。
真正跟顾老师熟络起来,是在毕业后,跟着沈启容一起去顾老师家蹭饭。顾老师喜欢海阔天空地聊天,他最大的乐趣似乎就是不断挑战对话者的常识。也许是跟他年轻时通过大量的翻译工作“自学”社会学有关,翻译的过程不就是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对话么。所以,跟学院派的社会学教授比起来,顾老师一直是在用一种看似“狡猾”则用思辨的方式来做研究的,而且这种方法背后应该是一种Peter Berger式的知识社会学自省吧。我猜测,顾老师后来主持的《大国方略》等一系列跨学科课程,也许就是他自己方法论的又一次实践。
给学生选择自由的导师
最后,一定要谈谈对我影响最大的导师陆小聪教授。前面提到,跟仇立平教授的提示有关,在时任文学院团委书记余洋老师(也是仇老师的学生)的牵线下,以“本科导师试点”的名义,将大二的我引荐给了陆老师。陆老师当时刚从日本归国,举手投足间还带着浓浓的东瀛味道,特别讲“规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毕恭毕敬地陈述了一些我的体育社会学思考,但也许是陆老师刚回国本就想多接触接触学生,我就有幸成了“陆家军”的第一个学生。
陆老师是个很有趣的人,从第一次在校园里见到骑着摩托车的帅气教授,到初次喝酒时给我讲授的日本礼仪,再到一起教学相长式地合作研究,直到我在德国读博期间他还亲自来德参加我组织的学术研讨会,师生间的互动故事上万字也记叙不尽。但作为学生,我最感念的是他开放包容的知识分子情怀:
来上大之前,陆老师就是体育社会学专家,有自己非常强势的专业领域。但如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浸润出来的那批大学生一样,陆老师有着丰富的阅读和思辨经验,加之日本的高等教育对于博士候选人的严格训练,使其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本就具有扎实的基础。初到上大的头两年,他带着我们几个学生(陆老师带的最初那两批学生)一本本地读社会学经典著作,有时候,我甚至都觉得是他读书比我们学生都更用功,他是在用自己擅长的西方哲学和熟悉的跨文化经验在跟社会理论对话。他要求自己不断地学习,他曾提过,身在上大社会学的共同体中,不能仅仅搞自己擅长的领域,还要能够跟其他系里的老师沟通合作,只有跟学科对话才能产生智识上的合力。
陆老师不仅仅是这么要求自己的,还鼓励学生们主动地去跟其他社会学教授学习请教。我曾经问他,别的教授都指导学生做跟自己的研究领域相关的论文,能够积累出一些成果来,为何他不给学生框定一个选题范围,而是任由学生选择跟体育社会学或城市社会学无关的课题?陆老师说也曾这么考虑过,但是他不想限制学生的选择。他认为,教育就是要给学生提供各种可能性,而教授就是应该给学生选择的自由。所以,他非但同意学生们的自由选题,还常常主动跟其他老师打招呼请教,或者动用个人关系给学生提供研究资源。包括我后来能够拿到奖学金去德国留学,也是主要得益于他通过日本导师联系的一位德国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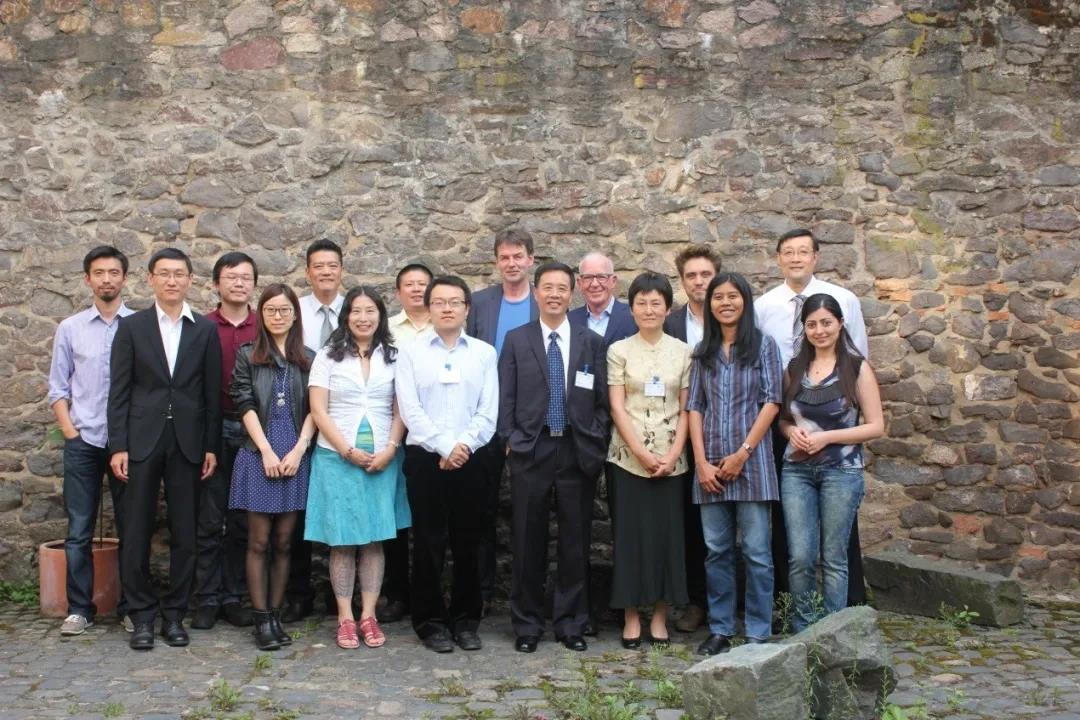
注:陆小聪教授应邀参加张修枫在德国组织的中德城市与体育发展工作坊
我在德国获得城市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后,陆老师曾经帮我联系过好几份高校的工作机会,还劳烦了系里的其他老师给我提供了帮助,我知道,他非常希望我能够在高校中发展,我们也曾设想过一些可以一起做的研究计划。然而,各种机缘巧合,我在等待某高校入职的时候,获得了去国内头部开发商工作的机会,对于做城市研究的人来说,有参与城市开发建设实践同样是一个巨大的诱惑。面对选择,我实在犹豫不决,还是去找导师求助。那天陆老师在高尔夫练习场打球,接到我的电话后,就直接让我去球场聊天。听完我的陈述后,他沉默了许久,告诉我说如果他在我这个年龄也很难选择,他也给不了我答案,但是让我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一旦选择了就不要后悔坚持下去。至于他曾经为帮我找工作托的人情啥的,让我不要有顾虑。在那一刻,我非常触动,陆老师不单单是在学术上,在人生道路上都一直包容和支持学生,这是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和导师的坚持:以开放的心态在理解他人并尊重他人选择的自由。
自十八岁至二十五岁,我在上大社会学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感谢师长们为学生们建造了一个开放多元的精神家园。篇幅有限,我就不一一记叙张文宏、张江华、耿敬、刘玉照等老师对我的关心帮助了。除此以外,我要感谢李友梅、张钟汝、范明林、翁定军、华红琴、章友德、李向平、徐新、陈友放等所有教授过我的老师们。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老师,才有了春风桃李,花开天下。


